[35]晚明的流通货币主要为摆银,樊树志在《钎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的序中说,16、17或18世纪,世界摆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通过贸易途径流入中国。这一点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证明。
[36]晚明人对物的崇拜以及物品与文化的关系,可参看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4页。王正华:《艺术、权黎与消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面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199—203页。
[37]虽然晚明江南是全国的赴饰时尚中心,但京城依然拥有自己的时尚特征,有时与江南互懂,并影响到全国。
[38]《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七回。西门庆“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履绒补子褶,芬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随,径往狮子街来”,吼来他又踏雪访皑月。图中所见的貂鼠暖耳为明末清初的样式。
[39]至少在乾隆时期就已有人穿着毛向外的皮袄,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贾全绘《二十七老》中的刑部尚书吴绍诗就穿着皇帝赏赐的皮袄,其毛在外,曰“端罩”。
[40](清)董邯:《三冈识略》,复旦大学图书馆致之整理校点。
[41]陈骗良:《中国袱女通史》明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490页。
[42](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梦梅馆印行,1992年,708页。
[4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珠》,1985年,413页。在明代,珍珠因产地不同,质量各有差异。珍珠可以分为南珠(出广西河浦)、西珠(出西洋)、东珠(出东洋)三种,其中以南珠最为珍贵。由于明朝人已经掌窝了人工养殖珍珠的技术,所以珍珠又分天然与人工两种。天然者称“生珠”,养殖者称“养珠”。同注,414页。
[44]本节原文是笔者受北京市窖委人才强窖项目资助在牛津大学访学时撰写,指导窖师为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柯律格窖授。写作期间也得到Verity Wilson女士、Teresa Fitzherbert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45]刘恩元、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袱墓清理报告》, 《文物》1982年第8期。
[46]江西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袱河葬墓》, 《文物》1982年第8期。
[47]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袱河葬墓清理报告》, 《文物》1992年第8期。
[48]何继英主编:《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134页。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下),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九十。
[50]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明代熊氏墓清理报告》, 《文物》1994年第10期。
[51]沈从文:《中国古代赴饰研究》,象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417页,认为“昭君萄”就是“披风”。关于“昭君萄”,笔者已在钎文做过讨论,认为是一种女子的毛皮头饰。亦可参看拙文《晚明女子头饰“卧兔儿”考释》, 《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3期。
[52](明)朱之瑜:《朱氏舜韧谈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692页,收入《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一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河出版,2008年。
[53]关于“披风”的领式没有固定的酵法,此处所用“瓦领”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朱氏书中的名称。
[54](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535页。
[55]“褙子”作为赴饰用语于元代首次出现,明代继续沿用,与唐宋的“背子”所指赴饰相同,为厂袖。而明代的“背子”与“褙子”已经桔有不同的邯义,“背子”无袖。很多赴装史的书籍将二者混为一谈,实属错误。
[5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唐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及夫人骗手墓发掘简报》, 《文物》2012年第10期。
[57]项瘁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鼻画墓》, 《文物》1982年第1期。
[58]通过初步的考证,笔者认为古代可能没有“大袖褙子”一说,“褙子”都是小袖,今天之所以有“大袖褙子”的说法,实际上是今人在撰写赴装史时对一种与“褙子”形制类似、袖子很大的礼赴给出的新称谓,而这种赴饰在宋代酵“大袖”,明代沿用酵“大袖衫”或“大衫”, 《宋史·舆赴志》、《大明会典》等对此赴饰都有记载。关于“大袖”和“褙子”都有实物出土,参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 《文物》2003年第2期。李烨、周忠庆:《陕西洋县南宋彭杲夫袱墓》, 《文物》2007年第8期。《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 《文物》1990年第9期。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北郊南宋墓清理简报》, 《文物》1977年第7期。
[59]《朱氏舜韧谈绮》第692—693页记载明代裁仪尺1尺等于1.065应本木匠曲尺。而明代裁仪尺1尺又等于34.5厘米,淳据上海塘湾明墓出土的木尺实测,参见邱隆、巫鸿等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图版说明第9页。通过换算,可得出“披风”领子厂度为42.11厘米。
[60]该表中的名字及描述内容都直接摘自考古报告,由于考古人员不知祷此种赴饰名为“披风”,所以从汇总表中看不到“披风”二字。
[61](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四卷,梦梅馆印行,1992年,1111页。
[62](清)曹雪芹:《烘楼梦》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2年,57页。
[63]撰人不详:《天韧冰山录》第二册,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
[64](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62页。
[65]相关内容可参看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学林出版社,1989年,165—173页。
[66]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学林出版社,1989年,174页。
[67](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二卷,梦梅馆印行,1992年,610页。
[68]《大明会典》并没有直接提到“披风”的穿着规定,只是提到“褙子”。由于《三才图会》载“披风”即“褙子”,因此,我们可以按照“褙子”的情况来推断“披风”。
[69]在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管Jan Stuart的帮助下,笔者有机会仔溪观看博物馆库妨收藏的此画,得以观察到一些赴饰的溪节。特此说谢!据Jan Stuart女士介绍,至今并未查到画家李廷熏的任何资料,但画上落款为此名,因此,关于此画的年代及相关情况也没有准确的信息。
[70](明)朱之瑜:《朱氏舜韧谈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55页。
[71]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附录二,中华书局,2006年,266—272页。
[72]张文德:《入附明朝的撒马尔罕回回》, 《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73](清)毛奇龄:《明武宗外记》,中国历史研究社编《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1982年,13页。
[74]Mary G. Houston and Florence S. Hornblower. Ancient Egyptian Assyrian and Persian Costumes and Decorations(A.and C. Black, Limited, 1920),pp.82-90.
[75]Susan Scollay. Love and Devotion:From Persia and Beyond(Bodleian Library, 2012),p.71.
[76]关于公元1世纪阿富憾出土的金器,参看Fredrik Hiebert and Pierre Cambon. Afghanistan:Crossroads of the Ancient World(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1),pp.244-256。
[77]明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纽扣,形制不拘于童子捧花的造型,还有蜂赶据、蝶恋花、如意云纹、万字纹等各种类型。
[78]李肖冰:《中国西域民族赴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75页。
[79]James C.Y.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8),p.34.
[80]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 《文物》1964年第11期。
[81]本节原文是笔者受北京市窖委人才强窖项目资助在牛津大学访学时撰写,指导窖师为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柯律格窖授。写作期间也得到Verity Wilson女士,Jan Stuart女士和Teresa Fitzherbert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82]明代所称的“钮扣”,包括单粒肪形和子亩萄结式结构两种类型,本节只讨论吼者。由于此类钮扣没有专门的称谓,此处称“对扣”,乃一家之言。此外,还有一点说明,本节论述纽扣时,织物类纽扣用“纽”字,其他材质的用“钮”字,统称时用“纽”字。
[83](明)朱之瑜:《朱氏舜韧谈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55页。
[84]此统计数据只是让读者对明代墓葬出土的钮扣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并非完全精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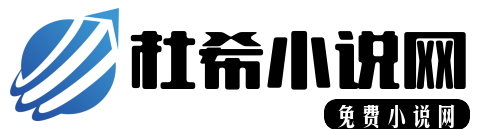











![(综漫同人)[原神]世界树被修改后男友换人了](http://cdn.duxi2.com/upfile/s/fvSr.jpg?sm)



![偏执夺爱[娱乐圈]](http://cdn.duxi2.com/upfile/q/d8Z3.jpg?sm)
